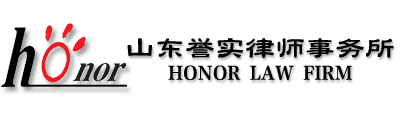【出处】《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1期
【摘要】“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给人当然不可罚的印象,因而“共罚的事后行为”的概念更为准确;在本犯行为因为具有违法性阻却事由、责任阻却事由、超过追诉时效以及在诉讼法上不能证明时,能够而且必须对事后行为单独进行评价;未满十六周岁的人盗窃财物或捡拾遗忘物,满十六周岁后故意加以毁坏的,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本犯教唆他人作伪证的,可能构成妨害作证罪;杀人后碎尸的,将侮辱尸体罪与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有助于减少故意杀人罪死刑的不当适用;间歇性精神病人伤害他人,恢复正常后不救助而导致他人死亡的,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
【关键词】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共罚的事后行为;法益;期待可能性
【写作年份】2008年
【正文】
我国刑法理论认为,不可罚的事后行为,是指在状态犯的场合,利用该犯罪行为的结果的行为,如果孤立地看,符合其他犯罪的构成要件,具有可罚性,但由于被综合评价在该状态犯中,故没有必要另认定为其他犯罪。 也就是说,之所以不另处罚事后行为,是因为事后行为已经被评价在本来的状态犯中;之所以不处罚盗窃犯事后毁坏赃物的行为,实质理由是,根据盗窃罪的规定在进行量刑判断时已经就盗窃后损坏财物的事实进行了完全性的评价,既然已经作为量刑情节一部分加以考虑了,若在盗窃罪之外另外适用损坏财物罪进行评价,则明显属于法律所禁止的二重处罚。 为便于讨论,下面把前行为称为“本犯行为”,后来的行为称为“事后行为”。
需要思考的是,(1)若本犯行为该当构成要件与否因为不能得到证明而不能处罚,但能够证明事后行为该当了某罪的构成要件时,若认为因为属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而不能对事后行为单独进行评价,是否产生了处罚的漏洞?例如,几个人共同销售赃物,现有证据表明其中仅有一人是盗窃犯,但不能证明具体是谁,若认为销售赃物的行为属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而且不符合刑法理论上的“择一认定” 的适用条件,则对这几个人既不能以盗窃罪定罪,也不能以销售赃物罪定罪,这种结论难言合理。(2)若本犯行为因具有违法性阻却事由或者责任阻却事由而不能作为犯罪进行评价,但事后行为具有某罪的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时,尽管该事后行为通常属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而不被单独评价,但在本犯行为因为上述事由不构成犯罪时,若还认为事后行为属于“不可罚”而不能单独进行评价,则结论难言妥当。例如,未满十六周岁的人实施了盗窃行为,在满十六周岁后毁坏该赃物,若认为本犯事后毁坏赃物属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则对行为人既不能以盗窃罪定罪,也不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论处,未必合理。事后行为完全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构成要件,若不定罪处罚,无疑是使实施了盗窃行为的本犯“身份”无条件地成为了事后行为的“免罪符”。又如,行为人捡拾遗忘物时未满十六周岁,满十六周岁后毁坏该财物的,若不将事后行为评价为故意毁坏财物罪也存在同样的疑问。(3)原本该当本犯构成要件的行为因超过追诉时效而不能定罪处罚时,还以行为属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为由不对事后行为单独进行评价,也不合理。例如,行为人实施的盗窃行为因为超过了追诉时效而不能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但盗窃后实施的故意毁坏赃物的行为完全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构成要件,而且没有超过追诉时效,这时若还认为盗窃犯故意毁坏赃物的行为“不可罚”,结论显然存在问题。(4)若认为本犯的事后行为当然地不成立犯罪,则对他人事后参与行为的评价可能也会带来问题。例如,本犯盗窃财物后,毁坏赃物时要求他人提供帮助的,若认为本犯毁坏赃物的行为不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构成要件,只能单独评价帮助本犯毁坏财物的行为,则使帮助成了“没有正犯的共犯”,即在缺乏正犯的情况下处罚共犯,这也存在疑问。只有承认本犯事后毁坏赃物的行为也属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正犯行为,才能对帮助毁坏赃物的行为以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帮助犯进行评价。需要说明的是,承认本犯事后毁坏赃物的行为属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正犯行为,并不意味着要对本犯处以盗窃罪定罪外还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论处,而是就事后行为本身进行评价而言。换句话说,若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实施了盗窃行为,满十六周岁后亲自毁坏赃物并让他人予以协助的,则对本犯的事后行为完全可以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正犯论处,他人以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帮助犯进行处罚。
由此可见,本犯的事后行为并非当然不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不成立犯罪、不可罚,因而有学者指出,将本犯的事后行为一概称为“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其实并不正确,准确地讲应是“共罚的事后行为”。 换言之,事后行为不是当然地不可罚,而是因为已由本犯行为所触犯的罪名进行了包括的完全的刑法评价;但在本犯行为因为具有违法性阻却事由、责任阻却事后或者超过追诉时效而不能定罪处罚时,完全可能单独评价事后行为。例如,未满十六周岁的人实施盗窃行为,满十六周岁后故意毁坏财物的,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又如,未满十六周岁的人捡拾他人财物,满十六周岁后故意加以毁坏的,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还如,本犯的盗窃行为虽然超过追诉时效而不能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但事后故意毁坏赃物的,完全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
还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一是,盗窃时因为未满十六周岁或者处于间歇性精神病的发病期,但在满十六周岁或者精神恢复正常后继续占有赃物的,能否以侵占罪定罪处罚?我国刑法第270条规定侵占罪的对象限于代为保管物和遗忘物、埋藏物,从一般人的法感觉看上述财物不属于“遗忘物”。日本刑法第254条规定:“侵占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其他脱离占有的他人的财物的,处一年以下惩役或者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科料。” 可见上述行为在日本可以构成侵占脱离占有物罪,而在我国或许存在疑问。从我国刑法第270条上看,侵占罪的对象包括了存在委托信任关系的保管物和不存在委托信任关系的无人占有的遗忘物、埋藏物,除此之外,并没有包括遗忘物、埋藏物之外的其他单纯脱离占有即无人占有的物, 因此,对上述行为以侵占罪进行评价还存在法解释上的障碍。或许毁坏上述财物时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而单纯继续持有时不构成犯罪,这显得不平衡。消除这种平衡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因为财物未被毁坏,单纯持有上述财物的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低于毁坏行为,因而作为民法上的不当得利进行处理就足够;另一种是将单纯继续持有的行为作为“隐匿”财物看待,并将隐匿行为作为“毁灭”财物的一种方式对待,从而也可以评价为故意毁坏财物罪。
二是,行为人毁损受委托保管的财物或者遗忘物、埋藏物的,能否评价为侵占罪与故意毁损财物罪的想象竞合,最终以法定刑重的故意毁坏财物罪处罚,以及未满十六周岁的人捡拾他人遗忘物,满十六周岁后加以毁坏的,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从而判处比侵占罪法定最高刑五年有期徒刑还要重的刑罚?盗窃后毁坏财物的,因为作为取得罪的盗窃罪的法定型高于作为毁弃型犯罪的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法定刑,因而事后毁坏赃物的行为能为盗窃罪的刑罚所吸收,即为盗窃罪所包括评价,不存在问题。但在侵占的情况下,认为法定刑远高于侵占罪的故意毁坏财物罪能为法定刑低得多的侵占罪的刑罚所吸收,存在疑问。 的确,发现公园长椅上被人遗忘的水果(不考虑价值),为了自己享用的目的拿回家后觉得味道不怎样就扔掉了,若在公园发现后当场吃下构成侵占罪,若拿回家后又扔掉了却构成法定刑要重得多的故意毁坏财物罪。行为人是当场消费掉和还是拿回家慢慢享用,对于被害人所有权的侵害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而且,若按照事后的故意损坏财物罪进行评价,则不得不说导致立法上将侵占罪的法定刑规定比故意毁坏财物罪低得多的意义完全丧失。 为此,日本学者山口厚开出药方:在因为超过追诉时效等原因而不得不对事后毁坏财物行为进行评价时,也只能在侵占罪法定刑的上限内处刑。 笔者表示赞同。因此,侵占行为人事后毁损财物的,在能够评价本犯的侵占行为时,不能以故意毁损财物罪进行评价;在因为超过追诉时效或者实施侵占行为时未满十六周岁而不能以侵占罪进行评价时,可以事后的故意损坏财物罪定罪,但处刑的上限不能超过侵占罪的法定最高刑五年有期徒刑。
国外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事后行为之所以不可罚是因为事后行为被包括评价在先行的状态犯中。在此意义上说,后行为是否属于该状态犯构成要件所预想的违法状态的范围(是否侵害了新的法益、危害结果是否超出了前行为已经造成的结果程度),便是区别不可罚的事后行为与可罚的事后行为的标准。例如,利用盗窃或者诈骗取得的邮局储蓄存折,欺骗邮局职员,使邮局职员以为行为人是存折的真实所有人,让其提出存款。这被认为是侵害了新的法益,构成独立的犯罪(成立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并合罪)。再如,盗窃物品后隐瞒真相出售给善意的第三者的,另成立诈骗罪。 可见,法益是判断事后行为是否可罚的一个重要标尺,以此为基准有下述一些问题值得思考。
第一、如何评价非法获取信用卡等银行结算凭证后的事后使用行为?本文以信用卡犯罪为例进行说明。我国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若认为本款中“盗窃信用卡并使用”包括了这种情形,即利用盗窃的信用卡在银行柜台提取现金或者持卡在信用卡特约商户冒充卡主签名消费的,属于“冒用他人信用卡”而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则该款规定是将本来符合信用卡诈骗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法律拟制为以盗窃罪论处。这样理解的话,盗窃本犯无论在什么地方使用窃得的信用卡,都只能以盗窃罪论处。但是,即便这样理解,也应该明白无论是在自动柜员机上使用,还是在银行柜台取现或特约商户消费,都侵害了新的法益。人们习惯于认为,使用盗窃的信用卡最终受损失的只是卡主,其实不然。银行和特约商户即便最终都能将损失转嫁给卡的主人,但银行损失的是现金,特殊商户损失的是商品。即便本犯是在自动柜员机上取款,银行也存在现金的损失。可以设想:若卡主信用卡被盗后及时到银行办理了挂失手续,但因银行职员的疏忽没有及时向银行结算系统输入相关数据,致使本犯在银行自动柜员机上不断地顺利取现,银行无疑存在现金的损失。需要强调一点,损失是否得到弥补与其法益是否受到侵害、是否犯罪的被害人,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这从国外刑法理论关于没有支付意思的人在信用卡特约商户消费如何处理的讨论中就可以看出。特约商户的损失通常都可以毫无障碍的从信用卡公司的事后无条件的划款中得到弥补,但刑法理论还是认为,特殊商户是被骗人乃至被害人。 另外,本犯窃得他人信用卡如不使用,则卡主只是损失卡本身的工本费价值,当本犯通过自动柜员机将卡主的钱转入自己的账号时,这时才算实现了债权性的财产性利益;当在自动柜员机上取现时,是将债权兑现为现金。这说明,本犯无论是在自动柜员机上转账还是取现,都是在窃取信用卡之后的对卡主法益的进一步侵害。从这个角度讲,即便本犯盗窃后在自动柜员机上使用信用卡也侵害了新的法益,按照共罚的事后行为的原理,本应评价为数罪(包括同种数罪),但因为刑法第196条第3款的法律拟制规定,只应对事后行为以本犯行为所触犯的罪名即盗窃罪进行包括的刑法评价。
第二,杀人后的碎尸行为能否在故意杀人罪之外另定侮辱尸体罪?司法实践中,杀人行为本身没有达到应当判处死刑的程度,但因为存在杀人后“碎尸”这种被认为极端残忍的情节,致使行为人被宣判死刑。应该说,这是无法律根据的、不合理的,是隐形的量刑观点事实上不当地起着重大作用的体现。 杀人罪是刑法理论公认的即成犯,将犯罪既遂之后的事后行为评价进本犯的构成要件中不妥当。就碎尸而言,不可否认符合刑法第302条侮辱尸体罪的构成要件,问题是能否将其与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日本学者认为,杀人犯单单将尸体放置现场不管的,不构成损坏尸体罪,但若为了隐匿罪迹而积极移动尸体加以隐藏的,可以成立不作为形式的遗弃尸体罪。 日本判例认可了杀人罪和损坏尸体罪、杀人罪和遗弃尸体罪之间的牵连关系。 本文认为,即便承认牵连犯概念,也不宜认为碎尸就是杀人行为的当然的通常的结果,评价为牵连犯未必妥当;本犯行为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事后的碎尸行为符合侮辱尸体罪的构成要件,按照共罚的事后行为理论,因为不能认为杀人罪已经对事后的侮辱尸体行为进行了包括的刑法评价;而且,不将事后的碎石行为评价为杀人罪的情节,有助于避免当前司法实践所存在的将碎尸行为评价为杀人罪情节的错误做法所导致的不当扩大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的现象。因此,故意或者过失致人死亡后又碎尸的,宜将侮辱尸体罪与故意杀人罪或者过失致人死亡罪数罪并罚。
【案例一】行为人杀害他人后,本来打算将死者身上不宜腐烂的物证——手表拿去找个安全的地方扔掉,但后来改变主意而将手表卖掉,问:行为人是否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侵占脱离占有物罪?
何为“毁弃”?如果采用“效用丧失说”,出于毁灭证据的目的将被害人身上的手表扔掉的,属于故意毁坏财物,此其一;其二,行为人拿走被害人手表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故不成立盗窃罪;其三,出于毁弃的目的后来产生占有的意思,按日本刑法能评价为侵占脱离占有物,在我国既不属于受委托保管的物,也不属于遗忘物、埋藏物,因而评价为侵占罪还存在解释论上的障碍;其四,出于期待可能性的考虑,本犯毁灭证据的不构成犯罪,但如果本犯所毁灭的证据属于他人所有的物,如行为人偷骑他人的摩托车作案,事后为防止罪行败露而将摩托车推入滔滔江水中,由于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无疑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正如,日本刑法理论没有争议地认为,虽然本犯伪造证据不构成犯罪,但如果伪造的是文书,则无可争议地构成伪造文书罪。
国外刑法理论通常将本犯教唆他人藏匿自己、毁灭、伪造证据与本犯教唆伪证分别论述,理由是后者的法益侵害性重于前者。日本判例自大审院以来,一贯坚持处罚本犯教唆他人藏匿、隐灭证据、作伪证的行为的立场。 日本学说上,关于本犯教唆他人藏匿自己、毁灭、伪造证据的可罚性存在积极说(教唆犯成立说)和消极说(教唆犯不成立说)
教唆犯成立说的理由是,既然被教唆者的行为构成犯人藏匿罪、证据隐灭罪,根据共犯从属性原理,本犯教唆的行为成立教唆犯是当然的结论;犯人自身藏匿或者隐灭证据因为缺乏期待可能性而不可罚,但教唆他人藏匿自己、隐灭证据,是使他人陷入犯罪,不能认为本犯教唆的行为还缺乏定型的期待可能性;本犯自己藏匿或者隐灭证据,属于刑事诉讼法所容许的被告人防御权的范围,但本犯教唆他人实施这些行为就已经超出法所放任的被告人防御权的范围,属于防御权的滥用;本犯藏匿自己、隐灭证据与本犯教唆他人帮助藏匿、隐灭证据对于刑事司法作用的法益侵害性存在显著的差异,后者明显高于前者。
教唆犯不成立说的理由是,立于共犯独立性说,正犯的行为不处罚,教唆行为也是实行行为,因而本犯教唆行为也不应受处罚;本犯作为正犯实施藏匿、隐灭证据的行为缺乏期待可能性,本犯以比正犯犯罪性更轻的共犯形式实施的更是欠缺期待可能性;本犯自己藏匿、隐灭证据不可罚,而本犯劝他人帮助自己藏匿或隐灭证据的行为属于本来的必要共犯的参与形式,按照必要共犯不可罚的原理,也不应处罚本犯教唆行为; 认为处罚本犯教唆行为的根据是本犯的教唆行为致使他人陷入罪责,但这是共犯处罚根据论中早已被淘汰的责任共犯论的主张,现在的主流学说在共犯处罚根据问题上采因果共犯论,因而以本犯让他人陷入罪责为由处罚本犯教唆行为存在疑问。
教唆犯成立说认为,伪证教唆行为对于本犯来说不能说没有期待可能性,或者本犯的期待可能性仅限于本法自己作虚假供述这种限度内的行为;宪法只是承认本犯自己具有拒绝作证的特权,而没有承认本犯具有教唆他人作伪证的权利;教唆行为制造了新的犯罪者,因而行为具有特别的反社会性;相对于本犯自己的供述而言,裁判官更容易相信依法宣誓的证人的证言,因而本犯教唆伪证比本犯自己作虚假供述对于司法作用的适正发挥的危险要大得多,日本刑法将藏匿犯人罪和隐灭证据罪法定最高刑规定为二年惩役,却将伪证罪规定为十年惩役,也说明了这一点;隐灭证据的行为通常是对物证的客观存在进行加工,而且隐灭证据的行为通常发生在法院开庭前,然而教唆他人作伪证是活生生的依法宣誓的证人直接在法庭上进行虚假陈述,其误导司法审判的危险相对于隐灭证据而言更直接、犯罪性也更高,因而教唆隐灭证据与教唆作伪证的犯罪性程度存在实质性差异;共同犯罪人作为证人能够成为处罚的对象,而将本犯教唆伪证排除在处罚的对象之外没有明显的理由;被告人之所以被排除在伪证罪的主体之外,仅仅是因为被告人不是适格的证人而已;本犯被排除在藏匿犯人罪和隐灭证据罪的主体之外,这从构成要件上就可以明显看出,而伪证罪是否仅限于他人刑事案件的证据,这从条文上并非也能明显看出;等等。 308
教唆犯不成立说认为,本犯自己作虚假供述的正犯行为因为没有期待可能性而不处罚,而作为共犯行为也没有期待可能性应该是因果共犯论立场的归结;从刑事政策上看,因为考虑本犯自己的正犯行为没有期待可能性,作为共犯行为也应认为期待可能性较少,因此,本犯教唆、帮助伪证的行为因为缺乏可罚的责任而不应受处罚; 既然认为期待可能性低,那么,本犯自己亲自实施与教唆他人实施应该同样考虑,而且,由于教唆比正犯的犯罪性低,因而以犯罪性低的共犯形式实施更不应具有处罚性; 551 “伪证教唆其实也是一种证据隐灭行为,若考虑到被告人欠缺类型性的期待可能性,仍然还是应该否定本犯教唆行为的可罚性。” 436
关于本犯教唆行为的可罚性,国内有学者指出,“原则上赞成当事人可以构成妨害作证罪主体的观点,但同时认为,对此也不能绝对化。以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为例。被告人本人作虚假供述的,不可能成立伪证罪,也不可能成立妨害作证罪。这是因为缺乏期待可能性,即不能期待被告人不作虚假陈述。所以,如果被告人采取一般的嘱托、请求、劝诱等行为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可以认为缺乏期待可能性,而不以妨害作证罪论处。但是,如果被告人采取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却他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则因为并不缺乏期待可能性,而认定为妨害作证罪。” “当事人教唆他人为自己毁灭、伪造证据的,不成立犯罪。……当事人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构成犯罪,与当事人教唆他人为自己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完全是协调的。即就严重妨害司法的犯罪而言,当事人的教唆作伪证的行为成立犯罪;就相对轻微的犯罪而言,当事人教唆他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不成立犯罪,具有实质的合理性。”
本文认为,以本犯教唆系陷他人于罪责的行为为由主张成立教唆犯,存在疑问,因为主张共犯的处罚根据在于使正犯陷入罪责与刑罚的责任共犯论因为存在致命的缺陷而广受批判,至今已经没有支持者; 共犯独立性说不能成为主张教唆犯不成立的理由,因为把教唆行为也看作实行行为的观点早已淘汰,不能以此论证教唆犯不成立;原则上讲,本犯自己作为正犯藏匿自己、毁灭、伪造证据因缺乏期待性而不受处罚,以比正犯犯罪性低的教唆形式实施犯罪的更不具有期待可能性,而且事实上,在逃亡路上本犯劝他人提供逃亡的帮助属于常态行为,按照必要共犯的理论,定型参与的必要共犯不具有可罚性;但是,由于我国刑法第307条第1款设置了妨害作证罪罪名,这个罪名可以看作是将部分伪证教唆行为正犯化,因此,在本犯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指使他人作伪证的,由于完全符合妨害作证罪的构成要件,没有理由不作为犯罪处罚。
日本刑法理论上的肯定说认为,本犯帮助其他共犯人藏匿、隐避,相对于本犯自己藏匿、隐避而言,法益侵害性要大;虽然本犯因为是刑事案件的客体而不能期待不藏匿、隐避,藏匿、隐避自己是防御权的体现,但本犯帮助共犯人藏匿的行为,不能认为还是缺乏期待可能性,不得不认为已经超出刑事诉讼法所容许的防御权的范围,而属于防御权的滥用。否定说认为,共犯人作案后不被发现应该说是共犯者之间共通的利益,本犯藏匿共犯者与藏匿自己同样类型性地缺乏期待可能性。 450
国内有学者认为,“犯罪的人窝藏、包庇共犯人的,应具体分析。如果专门为了使共犯人逃避法律责任而窝藏、包庇的,成立本罪;反之,倘若专门为了本人或者既为本人也为共犯人逃避法律责任而窝藏、包庇共犯人的,则不宜认定为本罪。但是,如果明知共犯人另犯有其他罪而窝藏、包庇的,应认定为窝藏、包庇罪。” 790但是应该说,以行为人的主观意图来确定窝藏共犯人的可罚与否还存在疑问。由于共犯人也是一种证据,窝藏共犯人也意味着隐匿证据,既然本犯毁灭证据不可罚,则具有同样效果的窝藏同案犯也同样不具有可罚性;从期待可能性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由此,上述案例二中本犯窝藏同案犯的行为不应构成窝藏罪。
对于本犯毁灭同案犯刑事案件证据的处理在理论上存在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共犯人的刑事被告案件,亦应视为他人的刑事被告案件,故上述行为成立犯罪。因为“共犯人”不是本人,只能属于“他人”。此观点受到的批判是,如果是单独犯则不处罚,然而因为有共犯关系则受处罚,这是不均衡的。第二种观点认为,共犯人的刑事被告案件,应视为自己的刑事被告案件,故上述行为不成立犯罪。理由是,犯罪人隐灭自己的犯罪证据而不可罚,是因为缺乏期待可能性;而隐灭共犯人的犯罪证据与隐灭自己的犯罪证据具有共同的利益,也缺乏期待可能性。但是该观点忽视了一个问题,即共犯案件的证据,对每一个共犯人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专门为了其他共犯人而隐灭证据,就属于隐灭他人刑事被告案件的证据,因而成立本罪;反之,如果专门为了本人、或者既为本人也为其他共犯人而隐灭证据时,并不缺乏期待可能性。另有学者提出的理由是,隐灭自己的证据之所以不可罚,是因为考虑到其处于被告人、嫌疑人的地位,所以,专门为共犯人隐灭证据的,应评价为隐灭他人的刑事案件的证据。但是,这是观点是用犯罪的主观内容来限制“他人刑事被告案件”,在方法上不能令人满意。 723
【作者简介】
陈洪兵,清华大学法学院2006级刑法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择一认定”是德国的一种刑法理论。德国学者举例说,在被告人处没有发现一套从物主处盗窃的首饰。该受盗窃罪指控的被告人辩解说,首饰是他从一陌生人处买来的;购买赃物符合窝藏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不可能对犯罪事实作其他解释。被告人要么实施了盗窃行为,要么实施了窝藏行为。在此情况下,同样应当适用“疑问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被告人即不得因盗窃,也不得因窝藏而受到裁判,而是应当宣告其无罪,因为就盗窃和窝藏这两个行为本身而言,没有哪一个行为得到证实。但是,这样一种分离的观察方法对于事实情况而言是不公正的,因为不管怎么说,已经得到证实的是,被告人一定实施了上述两个犯罪行为之一。在此等情况下,为了避免不正确的无罪宣告,在特定条件下适用较轻之法律(择一认定)。择一认定是一个出于刑事政策理由的“疑问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例外,而且,此等例外情况也适用于这样一些情况,即在这些情况中,不同的可能性不是存在于或多或少的层次关系中,而是存在于择一关系中。Vgl. Jescheck/Weigend, Lehrbuch de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5.Aufl.,Duncker & Humblot, 1996, S.144.
从这个意义上讲,杀人之后才产生获取被害人财物的意思而拿走死人身上财物的,在我国将其评价为盗窃罪或者侵占罪都存在疑问。因为躺在荒郊野外的死者身上的财物,既难言属于死者占有,也不能说属于死者的遗忘物。国内有学者主张将遗忘物作规范意义的解释,将死者身上或者身边的财物归入“遗忘物”,从而可以将拿走死者身上财物的行为评价为侵占罪。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726页。但笔者认为将死者身上的财物评价为死者“遗忘”物可能已经超出所容许的文字解释的射程范围。
【参考文献】
[1] 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68 .
[2] 平野龙一.刑法总论Ⅱ[M].东京:有斐阁,1975:411页以下.
[3] 井田良.刑法总论的理论构造[M].东京:成文堂,2005:455.
[4] 张明楷译.日本刑法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93.
[5] 虫明满.包括一罪の研究[M].东京:成文堂,1992:285.
[6] 山口厚.刑法各论(补订版)[M].东京:有斐阁,2005:311 .
[7] 山口厚、井田良、佐伯仁志.理论刑法学の最前线Ⅱ[M].东京:岩波书店,2006:246.
[8]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352.
[9] 井田良等.刑法各论[M].东京:ミネルブァ书房,2006:229页以下.
[10] 张明楷.结果与量刑——结果责任、双重评价、间接处罚之禁止[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
[11] 前田雅英.刑法各论讲义(第4版)[M].:东京大学出版会2007:499.
[12] 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新版第2版)[M].:成文堂2007:495.
[13] 日本判例:东京地判昭和62·10·6[G].判时1259·137.
[14] 小林宪太郎.事例16[J].西田典之监修.法学教室,2007(12)(总第327号).
[15] 立石二六.刑法各论30讲.:成文堂,2006:310.
[16] 东京リ—ガルマインド编著.刑法Ⅲ<各论>(第3版)[M].:东京リ—ガルマインド,2006:448页以下.
[17] 井田良等.よくわかる刑法[M].:ミネルブア书房,2006:206页以下.
[18] 西田典之.刑法各论(第四版)[M].:弘文堂,2007:423.
[19] 山中敬一.刑法各论Ⅱ[M].:成文堂,2004:786.
[20] 张明楷.论妨害作证罪[J].人民检察,2007(8).
[21] 张明楷.论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J].山东审判,2007(1).
[22] Vgl. Cramer=Sch?nke=Schr?der, Kommentar, Vorbem., §25, Rdnr., 20.